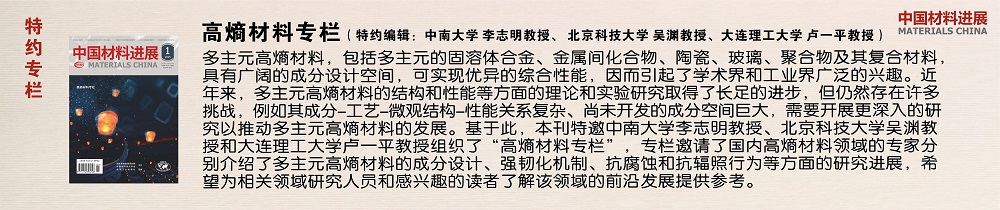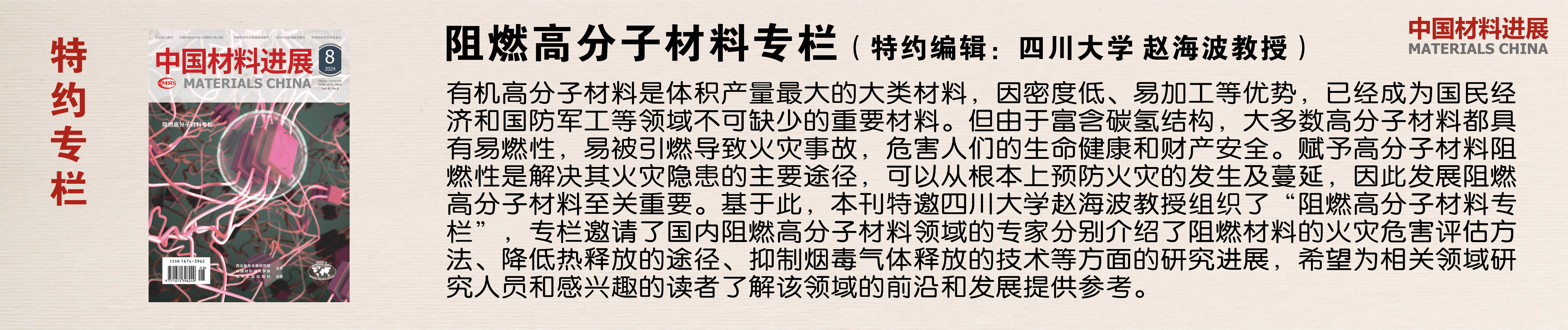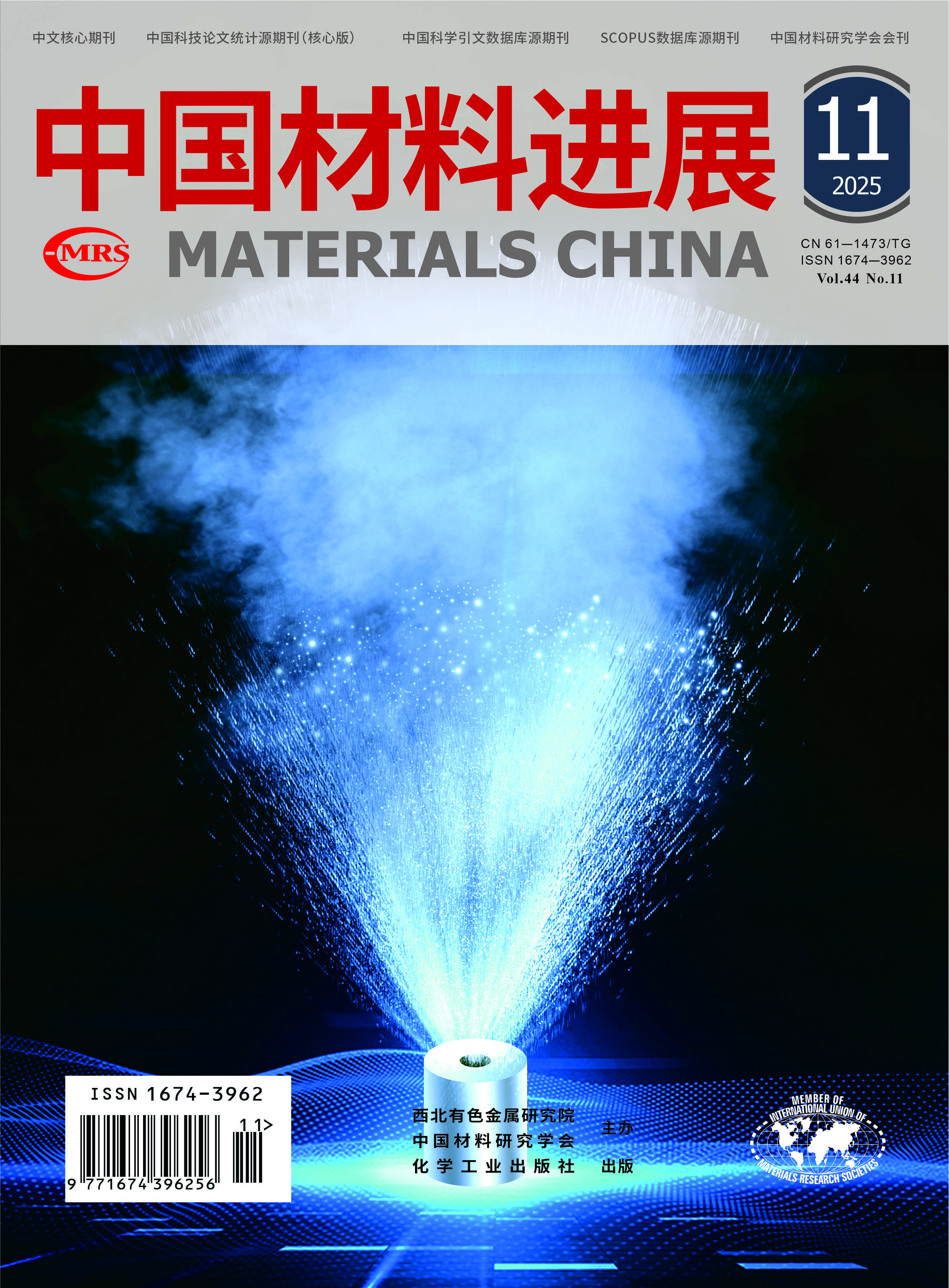導航鏈接
正文
《中國材料進展網》
中國科學院院士鄭蘭蓀:“量體裁衣”用好青年基金
發布時間:2022年5月30日 已經查看了1620次
第一次聽聞我國計劃設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博士后流動站時,鄭蘭蓀正在美國休斯敦的中國領事館。當時是1985年底,他正在準備回國事宜。
1986年5月,獲得博士學位沒幾天的鄭蘭蓀就回國工作了。當年年底,他便申請了某科研機構的青年科學基金,但遺憾的是未能獲批。他也因此遲遲不能獨立開展研究,“心中十分焦急”。
峰回路轉。1987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科學基金項目(以下簡稱青年基金)設立,同年,國家教育委員會設立“資助優秀年輕教師基金”,讓他有了盼頭。在首屆青年基金的申請中,鄭蘭蓀獲得了5萬元的最高額度資助,從此開始了原子團簇的科學研究。
在隨后的幾十年里,鄭蘭蓀對原子團簇的研究帶動了該領域在國內的發展。2001年,鄭蘭蓀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19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以下簡稱自然科學基金委)以“團簇構造、功能及多級演化”為主要內容設立了重大研究計劃。
答辯輕松
1977年是我國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次年,鄭蘭蓀進入廈門大學化學系學習。大學畢業時,他有幸考取了中美聯合招收的化學類留美研究生,并在該項目留學生中第一個學成回國工作。
他在美國師從碳60(C60)分子的發現者、美國萊斯大學教授Smalley,并參與了起步不久的原子團簇科學研究。Smalley因為C60的發現,于1996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987年,首屆青年基金是鄭蘭蓀申請的第一個研究項目,他為此準備的時間并不長。“當時比較單純,甚至都不清楚項目答辯后淘汰的比例。”鄭蘭蓀回憶道,答辯時,時任自然科學基金委化學科學部專家委員會主任吳征鎧慈眉善目,對后輩總是親切鼓勵、循循善誘,這讓他感到很放松。
鄭蘭蓀申請的青年基金的題目是“過渡金屬原子簇的激光產生及其結構與催化性能”。這是他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也是Smalley在上世紀70年代末創建的研究方法和開創的研究方向,在國際上也是“高精尖”的研究序列。
自然科學基金委化學科學部物理化學學科負責人張慧心很清楚該項目的研究內容和目標很難實現,項目答辯通過后便提前給鄭蘭蓀打了“預防針”。“國內的研究條件與國外不同,為了申請項目,可能將研究目標定得比較高,項目執行還要考慮實際情況和能力。”張慧心提醒道。
鄭蘭蓀一直不能忘懷張慧心等自然科學基金委工作人員對他的關心。后來,張慧心每次來廈門開會,都會到鄭蘭蓀的實驗室了解工作進展。“她站到高高的凳子上,通過我們自制的觀察窗觀看裝置的內部構造。她像長輩一樣關心著我的成長。他們身上體現了自然科學基金委優秀的工作作風和傳統,是激勵我們努力進取的強大動力。”鄭蘭蓀回憶道。
自制“國內版”儀器裝置
申請到5萬元青年基金的同時,鄭蘭蓀還申請到國家教育委員會“資助優秀年輕教師基金”,后者有8.5萬元。二者相加共13.5萬元。在上世紀80年代,這無疑是一筆較大數額的科研經費。但與建成項目計劃中的原子團簇研究裝置的花銷相比,經費差距仍然明顯。回國前,鄭蘭蓀認為“國內不太可能開展相關研究”,因此回國時并沒有攜帶任何技術資料。
這些經費不可能購買國外儀器甚至部件,而彼時國內的加工能力比較落后,信息又不暢通。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師孔繁敖、馬興孝、俞書勤等人的幫助下,鄭蘭蓀聯系上該校近代物理學教授王硯方,在其快電子實驗室研制出高速電子采集卡和程控脈沖發生器;后來,鄭蘭蓀又在孔繁敖的幫助下,聯系到中科院電子學研究所教授張多明,購置了微通道板離子檢測器。
鄭蘭蓀的母校廈門大學化學學科有著盡力扶持青年教師成長的優秀傳統。中國科學院院士蔡啟瑞和張乾二作為鄭蘭蓀博士后的指導教師,更是支持和鼓勵他獨立開展研究。
脈沖激光器是研究裝置中最難解決的部分。進口的激光器需要十幾萬美元。一個偶然的機會,鄭蘭蓀在《中國激光》雜志的廣告上看到蘇州一所中學的校辦工廠正在生產脈沖激光器。他根據廣告上的地址,在蘇州石路的一間老房子里找到這家“工廠”,僅花費5500元,就買下了這款脈沖激光器。神奇的是,這款十分簡易的脈沖激光器不僅能夠出光,而且可以脈沖觸發控制,能夠滿足他初步的實驗要求。
鄭蘭蓀在高考前,曾經在廈大物理系綜合電子廠等工廠干了多年的鉗工。他能夠完成儀器的機械設計,包括所有加工圖紙設計。Smalley對光機電、軟硬件無不精通,鄭蘭蓀讀研究生期間,還得其指導完成了整套儀器的安裝與調試。在獲得青年基金等項目的資助后,鄭蘭蓀“量體裁衣”設計了產生激光與研究原子簇的裝置。該裝置全部采用國產部件,完全由計算機控制和采集數據,是名副其實的自制“國內版”儀器裝置。
第一次試驗,儀器就采集到了信號。“現在回想起來,是十分幸運的,在獲得項目資助后不到一年就成功了。所有關鍵部件都是首次使用,只要有一個環節出問題,儀器不出信號,就很難調試和應用。”鄭蘭蓀說。
有意思的是,鄭蘭蓀還將裝置上采集到的原子團簇質譜,打印出來制作成圣誕卡寄給Smalley。看著這份僅為其實驗室十分之一價格的裝置制作出的“作品”,Smalley感到十分驚喜。
拿過好幾個“第一”
“我是幸運的。”鄭蘭蓀坦誠地告訴《中國科學報》。
在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人才項目上,他拿過好幾個“第一”。除了首屆青年基金以外,1992年他獲得了首屆自然科學基金委優秀中青年人才專項基金,1994年又獲得首屆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的資助。此外,他還成功獲得了霍英東教育基金、博士后研究基金等的資助,也都是首屆。幸運的背后是鄭蘭蓀日積月累的努力。
隨著經濟發展,科研經費的資助金額“水漲船高”,但“就像吃了3個包子飽了,不能說早知道只吃第3個包子”一樣,隨著時間流逝,鄭蘭蓀很難準確分辨每個項目各自的成效。但在他記憶深處,青年基金的意義始終無可替代。“這是我申請和答辯的第一項科學基金。”此后,他堅持不懈地扎根在原子團簇的科學研究上。
鄭蘭蓀注意到,時至今日,青年基金依然是絕大多數從事基礎科研的青年研究人員申請的第一個研究項目,是他們研究生涯開啟的第一步。“隨著中國基礎科學研究隊伍的快速壯大,相應的競爭肯定會越來越大,項目審批的標準也會越來越高。”
“青年基金應當鼓勵自由探索,提倡科學問題導向。青年科研工作者要能夠提出科學問題,敢于探索和創新。申請的研究項目要盡可能與申請者攻讀博士學位或博士后工作期間的工作有所區分和創新。從申請和執行青年基金開始,青年科研工作者應逐漸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乃至研究思想,提出乃至解決有意義的科學問題,扎實地邁出科學研究的步伐。”采訪結束前,鄭蘭蓀如是說。
日期 2022-05-30 來源:中國科學報